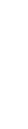峨峨丰碑
近代中医办学校、医院
民国时期,中医药界在抗争的同时,借鉴西医学教育,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不断改进自身,为发展中医教育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焦易堂等53位中委提出“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获会议通过。经多方努力,重庆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1939年5月公布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中医界抗争数十年的中医教育合法化取得了初步成果。1943年9月公布的《医师法》,明确将“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作为中医通过“检核”的条件之一。据统计,经过中医师检核委员会议认证,前后共有60所中医院校颁发的毕业证书获准通过检核。
近代医院形制源自西方,因民国时期对中医的歧视政策,由政府主持开办的中医医院极为少见。晚清时北京曾先后开设了内城官医院(1906年)和外城官医院(1908年),初以中医为主,后逐渐变为以西医为主体,1933年被改组为北平市立医院,成为了纯粹的西医院。1944年成立于重庆的陪都中医院为民国时期唯一纳入卫生行政系统进行管理的国立性质的中医医院。此外,南京的中医救护(济)医院,太原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苏州国医医院等亦由政府主办。这一时期,由民间力量开办的中医医院较有影响力,如中医学校所办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附属医院——上海广益中医院、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上海中国医院及广东中医药学校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等;中医团体或个人所办之丁济万的上海华隆中医院、杨浩如的养浩庐中医院及裘吉生的三三医院等。
【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中医史》
近代中医办学会、杂志
晚清以来,随着中西医之争日趋剧烈,出于争取行业权力、交流理论学术的需要,中医社团应运而生,遍及全国。据《中国医学通史》的不完全统计,1912—1947年各地创办的学会、研究会、医药改进会及中医协会、公会等约有240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1912)、中华医药联合会(李平书等,1912)、上海中(国)医学会(丁仲英等,1921)、医界春秋社(张赞臣等,192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吴公陶等,1929)、中西医药研究社(褚民谊等,1935),绍兴医学会(何廉臣等,1908),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阎锡山、杨百城等,1919),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承淡安等,1931),重庆国医学术研究会(谢全安等,1936)等。除上述学术性团体外,出于政府管理要求,中医职业性团体亦见于各地,如上海市中医协会(由神州医药总会、上海中医学虎、中华医药联合会组成,1928),北平市中医公会(施今墨等,1928),重庆的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张简斋等,1945)。中医社团在民国时期联系和团结业界,组织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通过积极创办期刊、开办中医学校与医院,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交流与行业发展。
与之同期,中医界创办出版中医杂志亦十分活跃。据统计,自1912年至1949年,民国中医杂志约有460余种,其中大部分分布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及中医密集的江浙、北京、广州等区域,其主办者多为中医社团、中医院校、中医杂志社及中医出版社等,影响较大的杂志有《中西医学报》《神州医药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三三医报》《医学杂志》《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等,是中医药行业信息流通的重要载体。
【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中医史》
民国中医融会新知
民国中医认识到中西医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与时俱进,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临床诊疗、中药学等方面,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医学的内容。如参照近代自然科学分类法,在1933年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中把中医学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何廉臣、史铁生主张仿照欧美先进国家治科学之法编写教材;1928、1929年曾两次召开全国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各地涌现的中医教材讲义有172种之多。再如,吸收西医解剖学、生理、病理学知识,但不强行融合。又如鼠疫,接受西说后,细化为腺性鼠疫、败血性鼠疫、肺鼠疫;开始尝试用西医知识来认识、解释鼠疫——由鼠疫杆菌经蚤类或鼠疫病人飞沫等途径传染。接受部分西医诊断法、诊断器械,如探喉镜、体温计、听诊器、脉压计、压舌板、X线摄片技术等;治疗上采用中西两法,如张锡纯石膏加阿斯匹林汤,中西药物联用;在时疫医院里,使用盐水静脉注射治疗霍乱;中医李建颐还发明二一解毒注射液,用于临床鼠疫的治疗。撷取西医部分药理学内容,对中药的研究也开始转向药物成分的提取、分析。在国家内忧外患、疫病流行以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融合的环境中,民国中医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社会防治疾病的中坚力量。
【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中医史》
“中医科学化”
1916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基于西医解剖、生理、病理之科学,对《内经》开展全面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目的在“堕其首都也,弃其本源也”,使中医理论土崩瓦解,将中医连根拔起。在时势的紧逼下,为了生存,中医界进行多种探索,改良、革新、科学化。其中“中医科学化”成为一时潮流,陆渊雷、谭次仲、谢仲墨三人的言论颇具代表性。陆渊雷早年追随恽铁樵,1930年代后,认为中医确有实效,但科学毕竟是真理。主张以西医学为参照,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解释中医。陆氏主持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起草《统一病名建议书》指出:“国医原来病名向来不科学……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之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能异于西医即不能合于科学”。谭次仲把“理真效确”作为中医学整理的标准,采用实验和统计的方法,将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理真)与中医疗效(效确)结合起来。谢仲墨认为科学化就是针对中医名实混乱,用科学原理解释,用科学方法整理,使中医成为有系统有程序的学问。将科学等同真理,用西医作为标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中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