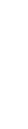峨峨丰碑
中医学术自有“立脚点”
面对严峻挑战,中医界有识之士从学理、医理上进行反驳、抗争。恽铁樵在《论医集·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中明确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五行最受当时科学人士的抨击。对此恽铁樵慧眼独具,指出“《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本源本于天之四时”,提出“四时之五脏”(《群经见智录》)的观点,认为五行是四时的代名词,不过是用来演说四时之变化,在方法论上中医自有立脚点,阐释了中医朴素辨证的认知思维,对责难中医的人们以强有力的回击。
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中医之思想方法,为《内经》之辩证法,而外医则为近世之机械论的方法,二者绝不相同也。”指出,《内经》的“最高理论为阴阳五行、生长收藏与调节,而以辩证法叙述之。故欲研究而理解其内含之精义,自以辩证法为最正确之途径。”认为《内经》的方法论(最高理论)是辩证法,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
陆士谔认为“凡是一种学术,必有其根据地,必有其立脚点”(《士谔医话》)。时逸人认为中医的特长在于“运用虚实寒热等为辨证之方针,选用历古相传之经验良方,尤注意于人体自然之机能,以及风土气候之变迁,方药之配合加减等”。辨证论治为中医立脚点已跃然纸上(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
【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中医史》
《中国医学史》的编撰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医学通史。作者陈邦贤(1889—1976),字冶愚,江苏镇江人,师从丁福保先生,为中国医史学的开拓者。陈氏有感于“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批判史等”,而“吾国为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遂“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中国医学史》),于1912年着手编写,其文章片段刊于《中西医学报》,1919年完稿,1920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刊刻行世,是为第一版。1914年,陈氏倡建了我国史上第一个“医史研究会”,邀众同道集思广益,修改补充,经修订后的第二版于1937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并由山本成之助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发行。全书约二十万字,共五篇十二章,依时间次序论述了上古、中古、近世及近代医学发展概况,并撰有疾病史专篇,书末附录中国历代医学大事年表。伍连德称其为“空前之杰作矣”。本书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亦为中国医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可行路径。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111,《百年中医史》,《中国中医药学术语集成 中医文献 上》P118
《中风斠诠》的编撰
《中风斠诠》为张山雷在研读张世骧(字伯龙)《类中秘旨》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所撰写的论述中风病的专著,成书于1917年。作者张山雷(1873—1934),名寿颐,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人,从学于朱阆仙先生门下,并在其师创办的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1914—1916)从事教务主任工作,编写各科教材。后到上海市行医,执教于神州医药专科学校,本书即作为授课讲义铅印成册。张氏后又于兰溪中医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在中医临床与教育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全书共三卷,卷一为中风总论,卷二为内风暴动的脉因证治,卷三为古方平议。本书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重视识病,主张“类中”之名不如径作“内风”。张氏虽推崇伯龙之论,但亦能指出其所失,如用镇肝滋肾之法当分次序,主张以“潜镇摄纳”为治疗原则,其“猝暴昏仆,皆是肝阳上升,气血奔涌”的理论为当时中医诊治中风病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29、282,《百年中医史》,《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 张山雷》P15
《中国针灸治疗学》的编撰 承淡安
《中国针灸治疗学》初版于1931年,因其深受读者欢迎,作者多次予以修订再版,不断丰富其内容,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至1937年已连出8版,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作者承淡安(1899—1957),幼承家学,尤精针灸,先后行医于苏州、望亭、无锡等地,有感于针灸一科,简捷万能而不被医家所重,日益衰落,当提倡之,遂编纂此书,并发起成立针灸研究社,兴办《针灸杂志》,应者颇多。全书(第8版)为承氏“收集各书,参以心得,益以最新生理,互为考证,删繁节要”而成,分为“总论”“经穴”“手术”(刺灸操作)“治疗”四篇,初步奠定了民国早期针灸学科体系的基础,为精确指示穴位,采用西医解剖部位与点穴后的人体照片结合展现,较之绘图更为真实。王逸桥称之为“针灸善本,学医之宝阀”,孙晏如赞之“以哲学之脑力,科学之眼光,将四千余年之国粹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至于经穴之准确,补泻之精详,非于此三折肱者不足道及也。从此后学得南针,医界又添辅助行书”。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54、56,《百年中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