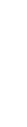峨峨丰碑
《验方新编》的编撰
鲍相環,善化(今湖南长沙)人,清道光年间曾在广西武宣任职,兼通医学。他一向重视收集经验良方,在自序中写道:“余幼时见人有良方秘不传世,心窃鄙之,因立志广求,不遭余力。或见于古今之载籍,或得之戚友之传闻,皆手录之。”。经过20年的搜寻和辑录,积累了大量的方药,又经反复筛选和精心考订,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验方新编》。此书是一部以医方为主,方论合参的方书。全书共16卷,书中内容丰富,各门俱备,卷1-8主要按人体部位,从头至足,分30余部及10余种杂证,论述内外治法、方药;卷9-16,按妇、儿、跌打损伤、内科诸证及怪症奇病等论述内外治法、方药。所收诸方包括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方面,外用方较多。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3240余方。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例如泄泻:寒泄,胡椒末和饭作饼敷贴脐上。或热柴炭布包敷。或炒盐敷。或糯米酒糠和盐炒敷。或酒炒艾绒作饼敷。或胡椒、大蒜作饼敷。或艾叶、灶心土、门斗灰、吴茱萸共为末,醋炒敷,均效。久泻不止,大蒜须加银珠捣融敷脐眼内,立止如神。因该书载方简便精博,切合实用,病者按人体部位对症查方,犹如磁石取铁,故自道光年间问世以后,屡经增辑刊刻,其中以抚渐使梅启照增补本最为突出,梅氏平家喜爱医药,热心刊刻医书。为使《验方新编》更好地流传,他仿此书体例增附诸家方剂,续增8卷,于1878年合编为《续增验方新场》24卷,增收3200余方(约分60门)。之后,长沙太守张浚如于1900年又对此书校订重刊,成为流传于世的主要版本。此外,尚有10卷本、16卷本、18卷本,先后刊刻者达数十种,广为流传,可见其对方便群众防病治病,普及医药颇有价值。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87
《望诊遵经》的编撰
清汪宏,字广庵,安徽歙县人。他认为非诊则无以知病知治,治病必须知诊,诊病必须遵经,并阐发望诊为四诊之首。于1875年著成《望诊遵经》,是中医诊断学中第一本以“望诊”命名的专著。全书共2卷,汪氏强调在诊断中可以因外知内,由此知彼,溯病症而知病源。汪氏在书中叙述了面部五官等与五色五脏的配合以及望诊与天地阴阳,南北高下,岁时气候,昼夜阴晴以至禀赋强弱,老少居养的关系。提出观察青赤黄白黑五种气色分布的浅表与沉滞,清爽与重浊,单一与混杂,集中与分散,润泽与夭枯等方面的所谓“相气十法”,即浮、沉、清、浊、微、甚、散、搏、泽、夭10种表现。主张望诊与声音、脉象、病症合诊。更从眼目、舌苔、口唇、牙齿、耳鼻、须发、头面、腹背、手足、毫毛腠理、皮脉肉筋骨、乳房、脐肾、阴茎以及汗血痰溺便月经、行止坐卧、身形意态等多方面缕述其望诊内容。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96
晚清中西医汇通学派
唐宗海—“折衷归于一是”
唐宗海,字容川(1846-1897),四川省彭县人。自幼苦读,通儒学而工书画,应科举而中进士。唐宗海因父亲体弱多病,故从小学习医术给亲人治病。他在治疗血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治验,归纳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虚”之四法。同时也深入研究医易之理,著有《血证论》《医易通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以上合为《中西六种》)以及《医学一见能》《痢症三字诀》等刊行于世,此外尚有未刊抄本《医柄》《六经方证通解》《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真可谓医术精良而通晓医理。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唐氏察觉到了中国医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看到了西洋医学的精巧,于是首先提出了“中西医汇通”,做到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从而达到“善无不备,美无不臻”的最高境界。
唐氏之所以倡导“中西医汇通”,是基于他认为:中西医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比如西医的血管即中医的脉。虽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求同方法,有着严重缺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论证中西医学必有可通之处,以及帮助中医运用西医生理解剖知识更好地理解中医的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唐宗海所处特定历史时代的影响,其思想限制着他对事物的认识深度和价值判断。具体来说,唐氏在主观上更强调“中医”优于“西医”,西医的解剖生理也完全未能超出中医经典著作的范围,甚至认为中医已超越了解剖阶段而进入更高的层次。把近代中医的明显不足归于晋唐以后,相关医著渐失真传以及宋元以来,书籍多有纰缪。正是这种祟古尊经思想,使唐宗海把西医知识作为解释中医理论的工具,把它纳入了中国训诂学的体系,生硬地将一些西医知识塞进《内经》等经典医著的框架之中,当用西医知识实在无法解释中医之理时,便武断地斥之为谬说,加以否定。这样的汇通方法,引出了不少荒唐无稽的结论,如以油膜释三焦等,显得十分牵强附会。
纵观唐宗海中西医汇通思想,其主张①“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美之医学;②中西医原理相通;③重中轻西,厚古薄今。在具体的汇通过程中,既有受时代所限引出的牵强附会,曲意文饰,也有从临证角度探讨汇通的崭新思路。所有这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唐宗海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朱沛文—“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县人。中医世家出身,其父兄皆为医,故他自幼随父学医,苦读《内经》《难经》多种医书,并临证施治20多年,具有较深厚的中医学基础和丰富的医疗经验。同时,他又生活在当时西方医学传播的兴盛之地广州,曾到西医院亲见尸体解剖及解剖图,同时精通英语,兼读华洋医书,对西方医学有一定的了解。这些为他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汇集《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书中有关人体结构、脏腑图象,与西方生理解剖知识、解剖图谱相互参照。
朱氏汇通中西医的指导思想,是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是非,不尽相同,不能偏主。”,主张将“华洋诸医之说,合而参之。”。在汇通过程中,采取了“通其可通,存其互异”、“不能强合”的谨慎态度。同时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朱氏对中西医有关人体脏腑器官的形态、功用的学说加以比较,提出脏腑官骸“形”、“体”多“从洋”,脏腑“气”、“用”多“从华”。他还比较详细地引述了中医经络系统理论与西医循环系统理论以及中西医对血的论述,既肯定中医经络学说为“医门要义”,又肯定西医血管论“确凿有据”。并主张中医“当兼究”西医的血液循环理论。因此他将西医解剖之“形”与中医脏腑学说之“理”结合起来,通过“兼采”“参合”的方法,以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建立“形”“理”兼备的医学。为了“参合”甚至采取了对号入座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的求同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
总之,朱沛文在其著作中,对中西医脏腑官骸形体功用,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对照与参合。可以看出,他关于中西汇通的学术观点、工作方法、研究态度,都比唐容川等前进了一步。但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朱氏对待中医、西医的态度是“参合”而不是“沟通”,不能归于“汇通学派”。”这些评论说明对朱沛文学术思想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中西医汇通的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总结。
此外,朱沛文在反对封建礼教和评价前人的成就与错误方面,也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在评价历史人物上,他并未一切以《内经》为标准,而是对宋代以后一些有重要贡献的医学家如刘完素、吴有性、李时珍等都予以肯定,同时,对陈念祖等人“率意嗜古”的思想也予以批判,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和求实的科学精神。因此,他被称为近代医学史上一位勇于探索的开明医家。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P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