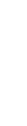峨峨丰碑
唐代中朝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无论在三国鼎立之时抑或新罗统一之后,中朝之间的交往都相当颜繁。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如《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校舍一千二百间……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蒋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语林》则记载:“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子弟人朝受业。”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学典籍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及中国的医事制度亦陆续传入新罗。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公元1433年由俞孝通等人撰写的《乡药集成方》85卷中,引用《广利方》达13处,可推测当时唐政府允许新罗使节抄回了《广利方》。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若毒气攻心,手足脉绝,此亦难济,不得已作此汤,十愈七八方……苏恭云:服得活甚易,但钻击(一作急)少时热闷耳。此方是为起死,是高丽老师方。”说明该方在唐显庆年间(656一660)之前已传入我国并广泛应用。又《唐会要》载:“贞元二年九月,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出商州,能愈众疾。上于禁中试用,有效,令编附本草,授思齐太医丞。”可见朝鲜僧在公元8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除医方之外,药物输入更为丰富,《唐会要》等文献记载了公元714一749年的35年间,中朝使节互访频繁,有时甚至“一岁再至”。此期间,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人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3
唐代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进步,成为亚洲各国学习的一个中心。而在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日本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因而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也带回了我国的医药成果。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同行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公元654年,日本进行“大化革新”以后,中日往来更为频繁,日本不断派遣唐使、学问僧、请益僧来我国。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公元7~9世纪的200余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计38船,有5000人左右,医药是双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时期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除前述惠日、倭汉直福音外,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梶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除派遗留学生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鉴真精通佛学,且兼通医学、建筑、文学、雕塑等。因治愈日本光明太后宿疾,更受日人信仰。被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汉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外,中国民间的有关习俗也在此时期由遣唐学生和学问僧传到日本。
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随着中国医学知识在日本的流传,日本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著作如《大同类聚方》《太素经集注》《药经太素》《摄养要决》《辅仁本草》等,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4
唐代中印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公元629-645年间,唐朝人玄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追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很丰富。该书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面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馔食:凡有馔食,必先盥洗,残宿不再,食器不传,瓦木之器,经用必弃……馔食既讫,嚼杨枝而为净……”“教育:七岁之后,渐授王明大论:……三曰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上述饮食习惯、口齿卫生、僧侣兼医、卫生习惯及医疗用药等均对我国有所影响。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25个春秋。在此期间,他不但用掌握的中国医学技术作为自我保健治疗的方法,而且向印度介绍了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唯斯色类是唐所需,自余药物不足收采。”反映了义净在中国本草学知识方面之渊博,而且对外来药之产地也很熟识。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就有11种。不少印度产药物亦作为贡品传入中国。来华之印度医则以眼科医为多。刘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通就是印度眼医一例。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及医方医法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均有述及。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两国医药交流之繁荣。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6
宋代政府重视医药
北宋历朝皇帝对于医学事业都比较重视,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通晓医学,史载他曾为弟弟赵光义用“艾灸炙背”,传为佳话。赵匡胤建国之初即命纂修《开宝本草》,赵光义在即位之前,就有搜集历代医方的爱好,即位以后,命王怀隐纂修《太平圣惠方》100卷。在雍熙年间,太宗还曾命贾黄中编《神医晋救方》1000卷,真宗时期重刻《道藏》,其中收录相当多的医学内容。仁宗时期,成立《校正医书局》,由高保衡、孙奇、林亿、孙兆等先后担任校正医书事宜,在古代断简残帛基础上,校正误字漏句,将我国重要医籍《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玉函要略方》、《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作了整理,使我国后世医家研读有所依据。同时还命王惟一铸造铜人,标定穴位,撰修《针灸铜人腧穴图经》,并刻石保存。这是自唐代我国针法一度不被重视,濒临失传情况下,重新得到重视的时期。
仁宗和神宗时,对医药人才的培养亦十分重视,医学教育较之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医局成为专管医学教育的机构。王安石变法实行“三舍法”,这是一种医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此外,还先后设立了“惠民局”和“和剂局”,前者以医疗为主,后者以合药为主。之后随着时代变迁,又将二局合并,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与之同时,各州府县还设立了安济坊、养济院、福田院等,收养老年病残者,一直延续至元代。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16